心向神州终不悔,为译消得人憔悴——缅怀译坛巨匠华兹生
本文作者:林嘉新,翻译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在站博士后、翻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中外文学关系与海外中国学。

2017年4月1日,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笔会翻译终身成就奖得主伯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以92岁的高龄走完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日本溘然长逝。斯人已逝,幽思长存,特撰此文,以作缅怀!

华兹生于1925年6月13日出生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市(New Rochelle, New York),是20世纪美国汉学界和翻译界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继韦利(Arthur Waley)之后,译介中国文学到英语世界最多的翻译家之一。华兹生的汉学译著囊括了中国古代典籍、诗歌、传记、佛经等诸多类别,而且还广泛涉猎典籍评论、文学论述等领域,多部专著、译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国代表性著作选集系列丛书》,成果斐然。先后于197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金奖(The Gold Medal Award),1981年于1995年,两次获得“美国笔会翻译奖”( The PEN Translation Prize)。2005年,美国艺术与文学研究院授予其“文学奖”,以表彰其多年翻译亚洲文学的努力与贡献。2015年,美国笔会中心为表彰华兹生一生致力于亚洲文学传播及其翻译成就,授予其“拉夫·曼海姆翻译终身成就奖”(The PEN/Ralph Manheim Medal for Trans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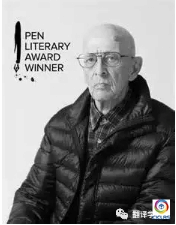
1. 教育背景
1943年,17岁的华兹生在新罗谢尔市高中毕业。此时正值二战后期,美国正在海上同日本作战,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和满腔报国热情,华兹生自愿选择加入美国海军,并被分配到一艘位于南太平洋的修补船上服役。两年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同日本的作战正式结束。根据战后国际形势的需要,美国政府决定在日本驻军以建立新的战后安全秩序。此时,华兹生所在的修补船正处于中太平洋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的埃内韦塔克环礁(Eniwetok Lagoon)。由于地理位置较近缘故,修补船于1945年9月驶往日本,驻扎在位于日本东京湾的横须贺海军基地(Yokosuka Naval Base in Tokyo Bay)。由于美国海军实行固定的休假制度,因此华兹生得以在休假时离开基地前往日本市区自由活动,也获得了接触、学习日语的机会。1946年2月,在完成为期三年的海军服役后,华兹生退役离开了日本,返回美国本土。
凭借《美国退伍士兵权利法案》 ,华兹生获得了一笔丰厚的教育津贴。日本的服役生涯使华兹生对东亚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心驰神往,也使他萌生了学习汉语与日语的想法。他曾谈到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知道我能够在这里学习中文和日文,而且我已经决定了要做一些与亚洲相关的研究;第二,因为它(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而纽约是我最喜爱的城市”(Watson,2001:1)。
由于中学时期出色的学业表现与自幼对东亚文化的执念,华兹生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院——哥伦比亚学院。哥大正式的汉语教授富路特 (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1986)正在中国休学术长假,汉语课都由英国传教士陆义全(Rev. A. Lutley)代上。由于英汉书写系统的差异巨大,学习汉字读写几乎占用了这群初学者所有的课堂时间,因为当时盛行一种观点,如果真要从事中国研究,可以日后再去中国学习汉语口语。在二年级时,富路特经常在课堂上介绍唐诗,并解释诗文的意思,这一教学方法激发了华兹生对译诗的热情,他经常在课后试图翻译这些诗作。在富路特的指导下,华兹生的汉语阅读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也为日后阅读较为难懂的中国古代典籍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本科毕业后,华兹生选择继续留在哥大修读中文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王际真(Chi-Chen Wang,1899-2001) 教授。在此期间,华兹生在翻译用语方面受王际真影响颇大,以至后来华兹生回忆他的教诲时,还能清楚记得其翻译主张:“译文不仅要做到语义准确,还要在英语文风上做到赏心悦目、行文流畅”(Balcom, 2005: 8)。研究生期间,华兹生选修了富路特的中国文献学(Chinese Bibliography),学会了如何利用《古今图书集成》 (Ku-chin t'u-shu chi-ch'eng)获取文献资料的方法。此时正值华兹生硕士论文选题之际,他决定尝试用自己所学的文献学方法来选择硕士论题。据其自述,“在阅读资料时,我碰到了‘游侠’(yu-hsia or wandering knights)这个词条,并感到十分好奇,于是开始查询文献……我在《史记》和《汉书》里发现两章专门讨论这一主题的章节”(Watson,1995:199)。当时,哥大东亚系鼓励学生采用自己的译作作为硕士论文,在王际真的指导下,华兹生以自己翻译的《史记》与《汉书》有关“游侠”的章节提交了硕士论文。此外,华兹生还在哥大结识了当时尚在修读汉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狄百瑞(William T. Debary),并与之结成了学术挚友,这为他后来的翻译生涯埋下了伏笔。
1951年,华兹生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硕士学位。此时,教育津贴已所剩无几,难以支持其博士学习,而没有博士学位,也不可能在美国觅得一份教职。出于个人学术兴趣,华兹生决定前往东亚国家游历。但由于战后中美两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对立,以及冷战格局的形成,华兹生中国之行的心愿化为泡影 ;国民党统治集团败退台湾地区后,采取了全面戒严、封锁政策,这也使他前往台湾的机会变得渺茫;当时香港的治安情况也堪虞,因此他在汉语地区工作的机会很小。故华兹生只能退而求其次前往同是东亚文明古国的日本,一则,日本在地理上离中国较近,二则,在文化和心理上与中国也密切相关。
战后的日本依然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镇,一大批从事中国古典文化研究的汉学家活跃于日本学术界。华兹生的日本之行得以成行还要归功于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 Yukawa Hideki) 和美籍日裔学者基恩(Donald Keene) 。汤川秀树曾于1949年在哥大做过访问教授,基恩曾在哥大求学多年,于1951年获博士学位。或许是因为他们与哥大的共同因缘,华兹生才得以与他们二人结识。在他们的帮助下,华兹生申请到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同志社大学的英语外教的职位,另一份工作是充任京都大学中文学系教授、著名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吉川幸次郎的学术助手。当时,吉川幸次郎的学术兴趣主要是中国古诗,包括唐诗与宋词,正从事中国文学中的对偶研究。作为其学术助手,华兹生的主要任务是将他的学术成果翻译成英文。由于该项目中有较大篇幅论述了杜甫诗歌中的对偶,使得华兹生第一次较深入地了解并学习了中国古典诗歌,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吉川幸次郎的鼓励下,华兹生申请到了京都大学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生课程(导师为吉川幸次郎),系统学习中国古典诗歌。

1953年,在吉川幸次郎的推荐下,华兹生申请到了福特基金会海外研究员( Ford Foundation Overseas Fellowship Program) 的资助。有了经费的支持,他放弃这两份工作,在日本全职从事汉学研究工作。由于硕士期间曾翻译《史记》的缘故,他选择了《史记》的研究课题。两年后,华兹生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写成了一套学术专著初稿,因此,他决定于1955 年夏返回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并以该课题注册入学攻读哥大汉学博士。在完成了一年的博士学分课程后,华兹生凭借其博士论文《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学家》(Ssu-ma Ch’ien: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于1956 年6 月获得汉学博士学位。经修改后,其博士论文于195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荣获哥伦比亚大学克拉克·费希尔·安斯利杰出著作奖 (Clarke F. Ansley Award)。这些汉学教育背景与研究经历为华兹生日后从事中国典籍翻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翻译缘起
二战后,哥大东亚系迎来蓬勃发展之时。一方面,由于战后国际战略与区域形势的需要,美国政府对于了解东亚国家国情的兴趣陡增,美国政府开辟了专门资金渠道招募亚洲研究学者以应对变化的国际形势。另一方面,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老牌强国的衰落,使西方国家对大学的教育经费支出大大减少,大量教授因高校教席裁撤,而不得不前往他国谋职,美国便成了他们的首选之地。
在这种背景下,哥大东亚系率先开设了研究东亚国家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的课程。为了解决汉学教材与相关书籍匮乏的问题,1950年,由刚开始崭露头角的汉学新锐狄百瑞主持的大型翻译项目“东方经典著作译丛”(Translation from Oriental Classics)得到了美国教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哥大出版社等机构的支持。这部教材系列集卷帙繁浩,入选的亚洲典籍多达几百部,语种主要涉及中、日、韩等多国语言,“专为非亚洲研究专家的普通读者和学生而译”(Watson,2011),旨在解决本科生教材的问题。或许由于曾同在哥大学习的缘故,狄百瑞很自然地便想到了昔日的学友、此时尚在日本游学的华兹生,让其也参与了一部分汉代文献翻译的工作。由于华兹生具有《史记》研究的学术背景,狄百瑞特邀他为《中国传统之源》(The Source of Chinese Tradition,1960)一书撰写了有关中国史学相关章节,并收录了华兹生译《史记》的部分内容。
3. 翻译成就
华兹生根据自己理解原著的难易程度,先后译出了《墨子概要》(Mo Tzu: Basic Writings, 1963)、《荀子概要》(Hsün Tzu: Basic Writings, 1963)、《韩非子概要》(Han Fei Tzu: Basic Writings,1964)、《庄子概要》(Chuang Tzu: Basic Writings, 1964)等四部先秦哲学著作。
华兹生还就五位中国著名诗人的近1000首古诗,出版了7本诗人专辑译著。分别是:《寒山诗100首》(Cold Mountain: 100 Poems by the T'ang Poet Han-Shan)(1962)、《宋代诗人苏东坡选集》(Su Tung-p’o: Selections from a Sung Dynasty Poet)(1965)、《陆游诗选》(Lu You , The Old Man Who Does as He Pleased)(1973)、《苏东坡诗选》(Selected Poems of Su Tung-p’o)(1993)、《白居易诗选》(Po Chu-i : Selected Poems)(2000)、《杜甫诗选》(Selected Poems of Du Fu)(2003)、《陆游晚期诗歌》(Late Poems Of Lu You)(2007)。
1971年,华兹生又陆续出版了介绍东汉至南宋抒情诗的著作:《中国抒情诗风: 公元2世纪至12世纪的诗歌》(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to the Twelfth Century)和《中国赋文:从两汉到六朝》(Chinese Rhyme-Prose: Poems in the Fu 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y Periods)。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兹生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选》(The Columbia Book of Chinese Poetry :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
4. 佛学姻缘
华兹生还具有深厚的佛学因缘。1975年起,他接受日本创价会(Soka Gakkai創価学会)的邀请,从美国远赴日本开始为学会承担翻译任务,主要是将日本僧人的佛教著作翻译成英语,其翻译的第一本佛学著作就是池田大作先生的《我的佛教观》(日文名:“私の釈尊絸”)一书。该书于1976年由纽约的John Weather Hill出版社以Living Buddha的英文书名出版。此后,华兹生陆续翻译了《维摩经》(The Vimalakirti Sutra, 1993)、《莲花经》(The Lotus Sutra, 1997)与《临济录》(The Zen Teachings of Master Lin-chi: A Translation of the Lin-chi Lu, 1999)等佛学著作(均译自汉语)。他还撰写了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白居易诗歌中的佛教因素》(Buddhism in the Poetry of Po Chu-I, 1988),也翻译了部分白居易诗,如《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之郎中张博士》、《睡起晏坐》与《白发》等篇目。
5. 译介效果与评价
华兹生的翻译成就使其蜚声学界,其译诗不仅受到了美国文学评论机构与专业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而且也影响了诸多当代美国诗人、汉学家与翻译家。
国际权威亚洲研究专业杂志《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盛赞其译文,“任何出自华兹生之手的古典名著新译本都应被当做一次大事件来对待,对其应满怀敬意地欢迎”(Watson, 2007: 封底)。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亚洲事务》(Asian Affairs)也对其大加褒奖,“华兹生具备大师级翻译家应有的所有品质,作为一名翻译巨匠与诗人,他启迪了两代人,其译作给予两代人以震撼”(Watson, 2007: 封底)。
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傅汉思(Hans Frankel)认为:“在当今还健在的人群中,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像华兹生那样用优雅的英文为读者翻译这么多中国文学、历史与哲学作品。从这位孜孜不倦的翻译家笔下译出的每一本新书,都让人感到如此地欣慰”(Frankel, 1986: 288) 。著名汉学家兼翻译家、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中文教授西顿(J. P. Seaton)在提及华兹生时,表现出极为仰慕之情:“他(华兹生)是一位多年来一直把翻译视为第一要务的学者。西方读者,尤其是文人墨客深受其译文影响(这点从莫温和斯奈德对华兹生译作的封面评论可知),在这点上几乎没有任何在世的汉学家可与之媲美”(Seaton,1985:151)。这点也得到了著名翻译家、美国《唐学报》(T’ang Studies)主编、科罗拉多大学中文教授柯睿(Paul W. Kroll)的赞同:“毫无争议,华兹生是本世纪在中国文学英译领域最高产的翻译家。他出版的书籍的名录很长,包括近两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哲学、历史和诗歌。他堪称我们时代的奥古斯特·费茨梅尔” (Kroll, 1985:131)。
美国汉学家白牧之(E. Bruce Brooks)与白妙子(A. Taeko Brooks)教授也称“华兹生的译文具有众所周知、备受公认的优点——即翻译用语平易口语化,内容通顺连贯,以至于几乎不需要解释”(Brooks, 2009:165)。美国汉学家柯夏智称,“隐匿于华兹生质朴的译诗诗行之下的不仅是其作为学者的多年学术积淀,也是对当代美国习语的内化恪守”(Klein, 2014:57),“其过人之处就在于译诗弥合了诗歌与学术的分裂”(同上:58),“译作为在英语世界建构中国古诗的传统,实现英译汉诗经典化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朱徽, 2009:203),“堪称当代中国古诗英译之典范”(冯正斌等, 2015:104)。
美国“垮掉派”文学运动领袖、著名诗人斯奈德(Gary Snyder)也对华兹生推崇备至,并给予其译诗高度评价:“华兹生是本世纪最出色、最执着、最慷慨的中国文学译者”(Watson,1994: 封底),“相对而言, 华兹生使用了较文雅的英文来翻译,而不像我那样野性” (Leed, 1986: 178)。当代诗人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也曾经做过些文学翻译,但对翻译实践,尤其是面对华兹生这样的译者时,他显得格外谦虚,“我曾经翻译过一些东西,大多翻译是在许多年前做的,正如世界上有钢琴家与会弹钢琴的人之分一样,世界上有翻译家和从事翻译活动的人。华兹生正是一位翻译家,而我却最多算是个半吊子”(Errington, 2011)。
6. 余论
华兹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译介是当下中美文学关系、中美文化关系史上的重要个案,也是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从其译介效果与文化影响力上看,其经典程度与重要性绝不亚于理雅各、韦利、庞德等翻译家,此外,因其是当代译者的缘故,研究其翻译活动还具有当下意义。华兹生身为翻译中国古典文化的泰山北斗,译介影响力很大,但时至今日,华兹生的翻译成就尚未能起国内学界的足够关注,至今未出现研究华兹生翻译活动的专著,研究其翻译论文也仅有寥寥数篇,这与华兹生的翻译巨匠地位极不匹配。总之,华兹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译介活动兼具经典性、接受性与当下性,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典范意义,对其展开研究必将对中国文化外译战略提供重要启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文学译介内在规律的思考,对中美文学关系研究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为翻译家,华兹生必将名垂青史,其翻译功绩也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闪耀永恒的光芒。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翻译学研究”推送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NjgxNjYzNA==&mid=2247483904&idx=1&sn=3d2fc3a24fc341132dca08857121f6a5&chksm=e86be515df1c6c03e99711dc95a70a2e7d3aed29fb32189087e4213ca33790c644be666f2d46&mpshare=1&scene=23&srcid=0405jqEx2zNkcUZEAMbjNZnR#rd)